在香港書展期間,傳出高馬可教授(Jonh M. Carroll)的《香港簡史》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,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。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,不過論敏感,《香港簡史》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。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,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,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。
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,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。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,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。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,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。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,"(not)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"。
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,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。穆黛安(Dian Murray)及安樂博(Robert Antony)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,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。他們有獨特的文化,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。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,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,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,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。於是,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,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,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,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。據陳偉群博士考據,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,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。
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,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。我們不要忘記,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,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,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。而中國這個帝國,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。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,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。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,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。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: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,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;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,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,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。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,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,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。
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,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,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。這種香港經驗,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。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,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,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。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,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。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,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,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。與此同時,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。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,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,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。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,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,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。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,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。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,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。
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,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。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,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。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,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、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、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、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。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,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。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,而港府亦投桃報李,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,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。
本書顛覆之處,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,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。而香港的本土意識,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。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,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,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。可是,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,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,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。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,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。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,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,得到自己的生命力。
《明報.星期日生活》2013年7月21日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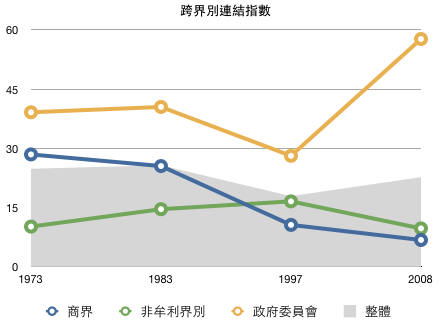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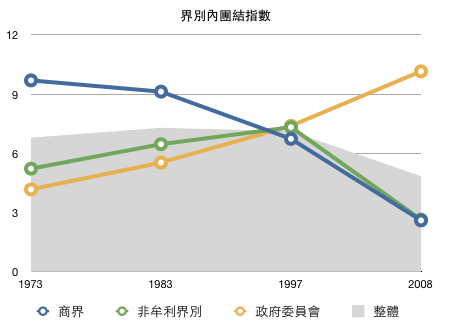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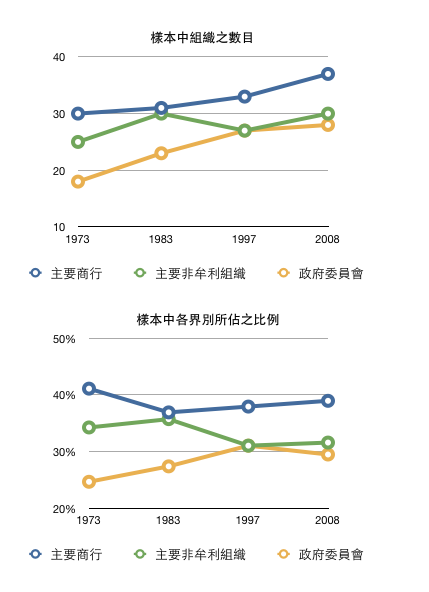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你必須登入才能發表留言。